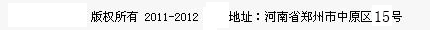■本报记者杨书源年1月13日,24岁女大学生吴花燕病逝。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,一个募捐疑团让死亡又多了一层悲凉——儿童紧急救助中心(以下简称)曾在网络募捐时夸大她的生活困境,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,以她的名义筹得近万元,但实际用于小吴救治的款项仅2万元。公益项目以帮助这位贫困女大学生为借口,操纵苦情戏码,已经走向了公益的反面。吴花燕离世后,的创始人郑鹤红决定实名举报这个项目几年来的违法违规行为。互联网公益的外衣下,一层层光怪陆离的伪装外衣被扒开,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(以下简称儿慈会)老牌公益项目的乱象暴露在了聚光灯下。万“苦情筹码”去年10月看过吴花燕互联网筹款文案的人,会记得文案对这位寒门学子不忍卒读的描述:吃馒头充饥,有时一天只敢吃1个馒头;吃糟辣椒下饭,因为这种辣椒最便宜。身高厘米体重43斤、父母早逝、寄人篱下、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弟弟相依为命——文案中,吴花燕俨然蜷缩在“阳光照不到的角落”,被生活压弯了腰、靠低保苟延性命。发布的文案出现在水滴筹和微公益上。两个平台的最终募捐总额是万元。另一重真相却在这个文案中被湮没了。根据吴花燕就读学校——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在她离世后发布的公报,吴花燕在校期间共接受过元资助,其中包括住院前的元和住院后的元。吴花燕也在生前接受媒体视频采访时表露:自己的境遇没有捐款文案所说那么不堪。因为精准扶贫政策和学校、老师的帮助,她平时也绝非靠元低保度日,并且她的大部分医疗费用是通过医保解决的,而非自费。信息为何出现如此大偏差?从此后的捐赠结果反推,这或许并非无心,而是有意。的工作人员曾为她带去2万元善款,直至她离世,这个数字也没有增多。而实际上以她的名义筹得的数字是这个捐款额的50倍,万元。剩下的98万元去了哪儿?1月14日晚儿慈会发布公告中称:转款的2万元分别来自微公益和水滴筹,各是1万元,用于吴花燕的治疗。根据吴本人和家属的捐款使用要求,余下的款项留着手术和康复时使用。但是吴花燕的亲属都否认了这种说法,并表示自己对余款一事毫不知情。郑鹤红说:“其实那个募捐文案一出,我就看透了。一个孩子在获得学校社会的资助后,每个月大概能有0元生活费,怎么会连饭都吃不饱?这就是这几年的惯用操作,夸大患者的困难,但是对受助者已经从社会救助体系中获得的资源绝口不提,这样有助于为募捐设置较高金额。”她是在去年10月为这次筹款事宜中的“蹊跷”发声的,但是当时呼应的声浪很小,甚至还有人讽刺她“见不得人好”。而眼下,站在她身边的人似乎多了起来。郑鹤红认为,这次吴花燕也毫无疑问成了用慈善捐款敛财的工具。“在她本人生前并不知情的情况下,夸大其生活遭遇,在多个平台发起相同案例的项目捐款,其实这是一种超额募捐,目的是囤积捐款。公益机构可以用这笔钱去理财,从而获得收益。而这部分收益是可以不用于慈善捐款的。”郑鹤红推测。而根据慈善法第五十七条规定“慈善项目终止后捐赠财产有剩余的,按照募捐方案或者捐赠协议处理;募捐方案未规定或者捐赠协议未约定的,慈善组织应当将剩余财产用于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慈善项目,并向社会公开。”郑鹤红透露,从一年半前开始,自己和不少的资深志愿者成立了监督小组,到目前她们已经向民政部提交了近20个证据链比较确凿的违规募捐项目。这些项目有不少相似性,比如都会选择那些病情危重不治,家中条件很差、没有能力跟进慈善捐款进程的患儿家庭作为捐助对象。另外不少问题募捐案例也出现了:同一个受助者信息,同时在多个线上募捐平台上,以相同的捐赠款用途、数目募捐。“有的个案,大概是害怕信息雷同太张扬,就会给孩子换个小名刊发出来。”郑鹤红说。在志愿者的统计中,公开募捐的数百名病孩中,最终死亡的比率超过了30%。而根据郑鹤红长期从事儿童救助领域方面的经验判断:在随机不可以挑选病种的情况下,如果社会公益的力量有效介入,患儿的死亡率绝不会那么高。捐款去了哪儿?根据公开资料,儿慈会是年1月12日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。主要宗旨在于募集社会资金,开辟民间救助渠道,救助有特殊困难的少年儿童,资助和促进民间公益慈善组织为少年儿童服务。而则是儿慈会主打的自主项目。
公益募捐苦情戏疑团中国经济网
发布时间:2024/3/13 21:10:11 点击数: 次